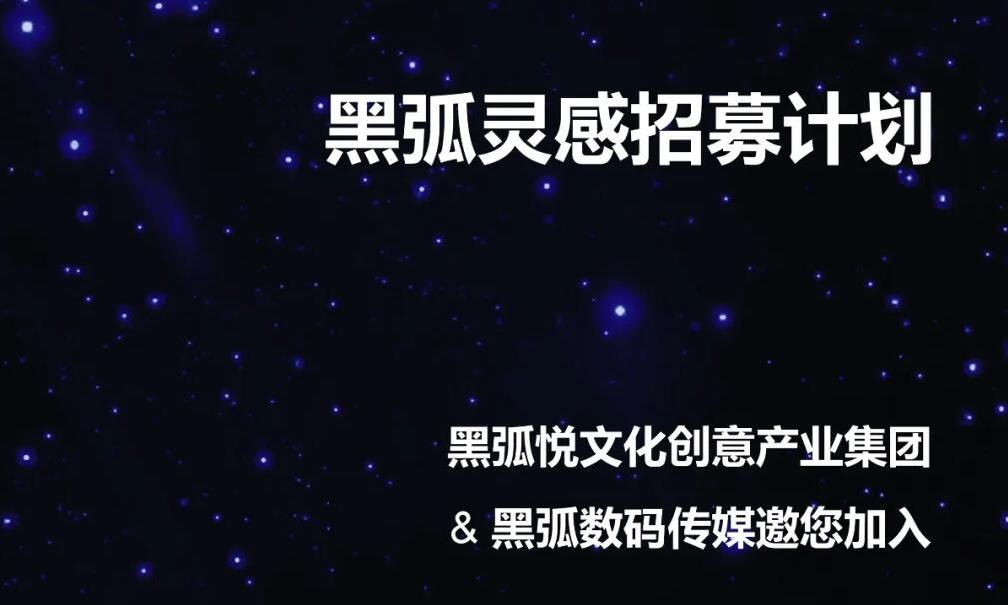来源于:新传研读社 ,作者:新传研读社
用有趣推倒学术的墙,让传播学得以传播。
一篇优秀的研究论文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困难,几乎任何的论文都会包含这些“小节”:(1)文献综述(2)搜集数据(3)检验数据(4)讨论研究发现。
诚然,所有的研究者都必须遵守这些塑造科学气质的规范和价值观。不过,你是否也会隐隐觉得,期刊上发表的传播研究越来越……无聊了?
在SSCI期刊《信息、传播与社会》中《拒绝枯燥:传播研究中,有趣意味着什么?》的作者Manuel Goyanes看来,一份真正优秀的研究,不仅需要追寻真理,同时也要在某些重要的层次上挑战读者的既有认知;他不仅要遵循科学研究的准则,更要通过迷人的技艺与设计,超越这些准则。当然,就像艺术一样,有趣的研究是流动的、气态的。
本期摘取论文中的主要论点,带你一览一份有趣的传播学研究,看看它究竟长啥样?
为什么有趣很重要?

在我们讨论“何为有趣研究”之前,似乎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有趣真的那么重要吗?
显然,在很多学者看来,“有趣”并不是他们判定一项研究最重要的指标,甚至根本就算不上一个指标。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有趣是以牺牲学术研究的规范和准确性为代价的,它便一文不值。不过,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方法的严谨、写作的规范,那么,很可能我们会制造出一大批看似精美,实则无用的琐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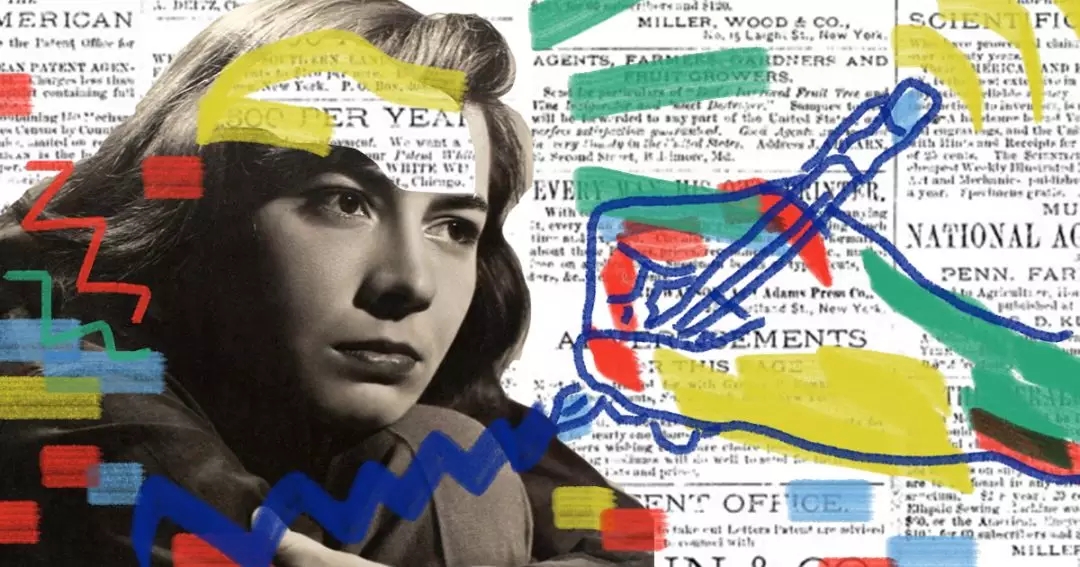
在Manuel Goyanes看来,传播学研究越来越流行的论文套路便是:精致的无用。
实际上,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在公开或非公开的场合质疑我们这个学科的价值:在“不发表就出局”的机制框架下,研究论文越来越像是一种商品:它是标准的、大规模生产的,到头来又是枯燥和无聊的。糟糕的写作技巧随处可见,而且越来越公式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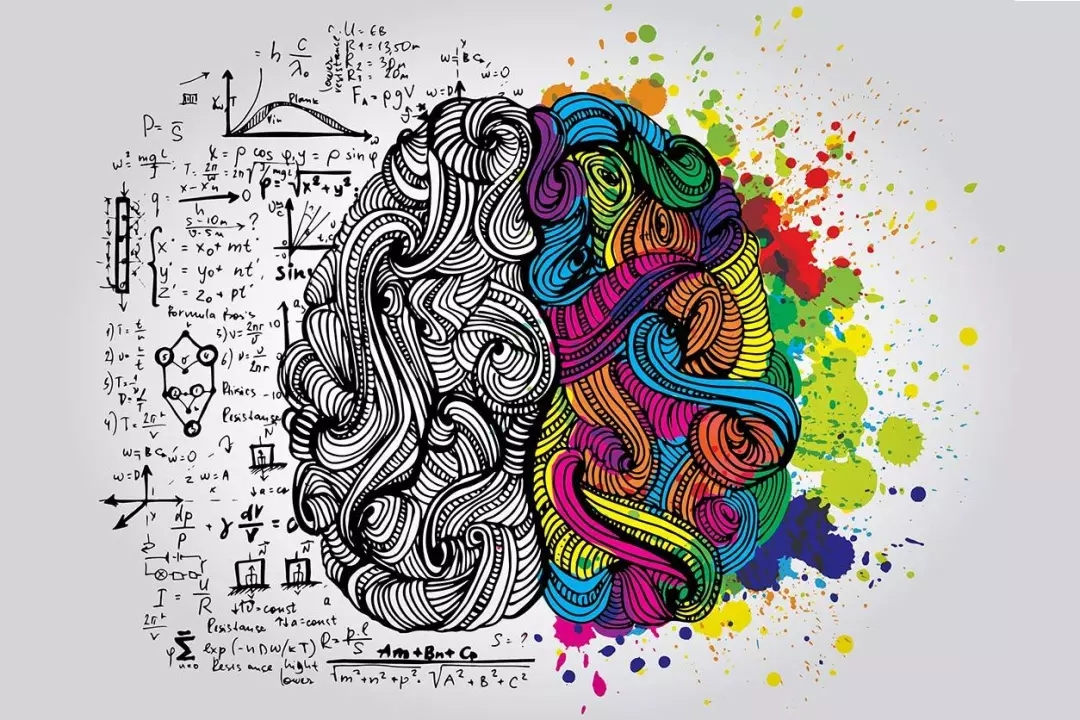
很多学者恐怕都会同意这一观点,不过,他们对此好像也无能为力。似乎这就是撰写研究论文唯一的方式,也是主流传播学期刊唯一能够接受的方式。在这种背景之下,想要变得“有趣”,似乎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情。真的如此吗?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Manuel Goyanes向16家传播学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发送了电子邮件——我想知道,在这些学者眼中,什么样的研究可以算作“有趣”?又有哪些具体的论文,被他们觉得符合“有趣”的标准呢?
当我们谈论“有趣”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基于16家传播学期刊88位编委会成员的访谈,Manuel Goyanes发现了五种类型的“有趣”。
反直觉(counterintuitive)研究
学术把关人们认为,那些挑战读者既有认知的研究是有趣的。其中包括挑战既有理论、提供反直觉的发现、打破读者预期假设。
反直觉的研究通常会遵循以下原则:(a)指出某一个文献领域(b)指出并说明这个领域中通常的假设(c)评估这些假设(d)开发一种可能的替代性假设(e)考虑这种替代性假设与读者的关系(f)评估这些替代性假设的基础(Alvesson & Sandberg, 2013)。
在反直觉研究中,一个精彩的例子是Dearing(1995)对那些标新立异的科学家的考察。人们往往认为,记者在报道这些极具争议的科学时还会保持“虚假的平衡”(false balance),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科学界的边缘人物正在努力获取合法的真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记者维持平衡仅仅是因为,这个职业要求他们这样做。
▶范文:Dearing, J.W. (1995). Newspaper coverage of maverick science: Creating controversy through balancing.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4(4), 341–361.

奠基性的(foundational)研究
学术把关人们认为,那些能够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论文是有趣的。其中包括对一种现象提出新的实证证据、对一个领域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以及那些先锋式的研究。
奠基性的研究之所以有趣,因为它们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包”。它们会因为自己出色的解释力,从而被广泛引用,不管是为了支持一个观点、修正一项假说,还是在另一种场景中完成自我挑战。
McCombs和Shaw(1972)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便是具有奠基性意义的,不仅是它修正了有限效果论,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观察媒介效果的新角度——让我们暂时离开对于行为的观察,专注于媒介对认知(重要性)的影响。
▶范文:McCombs, M.E., & Shaw, D.L. (1972).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 (2), 176–187.

新路径的(new approach)研究
学术把关人们认为,这些研究提供了理解(数字)现象的新方式、整合了不同的思考视角、使用其他领域的新视角来解释数据,并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重新验证经典理论。
有两种最常见的“新路径”。其一是使用一种既有的理论去验证我们生活的新(数字)环境,再反过来去检验这个理论。这种思路遵循着一种“解释逻辑”,它提出的问题,本质上是“what if”。

例如,研究者会把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放置在社交媒体的环境中进行检验——人们是如何在朋友圈中进行印象管理呢?亦或者是,正如我们在之前的推送中提到的,在人机交流(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的研究中,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检验既有的人际传播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还是适用的。
第二种“新路径”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解释传播学现象。对于传播学而言,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都是我们经常会借鉴的学科。通过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借用,我们可以将不同的理论传统进行嫁接,进而加深我们对于传播现象的理论。

Shrum(1996)对培养理论的研究就是开拓“新路径”的典范。在研究中,Shrum借用了既有的心理学理论和实验方法,解释了电视培养效果背后的心理机制。
▶范文:Shrum, L. J. (1996).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underlying cultivation effects further tests of construct accessibilit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2(4), 482–509.
高质量的典范
(quality and exemplarity)论文
这种有趣有趣的论文包含以下特征:(a)它们大多是量化的、遵循假设-演绎路径(b)具有扎实的数据分析(c)对社会及时并有益(d)对未来的理论发展和实证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讲,高质量的典范论文都在检验、延展和建立新的传播理论。
高质量的典范论文都是标准化的,之所以说它们有趣,因为他们将研究过程的技术严谨性最大化,提供了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实证证据。这一类的研究往往是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例如比较性分析和全球调查。
例如,Hanitzsch(2011)考察了新闻业的职业环境,可被视作是一种高质量的典范研究,因为它的研究数据基于超过18个国家、超过350家新闻机构、1800位记者的问卷调查。这一调查对媒介体系和新闻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同时也是典范性的跨国研究。
▶范文:Hanitzsch, T. (2011). Populist disseminators, detached watchdogs, critical change agents and opportunist facilitators: Professional milieus, the journalistic field and autonomy in 18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3(6), 477–4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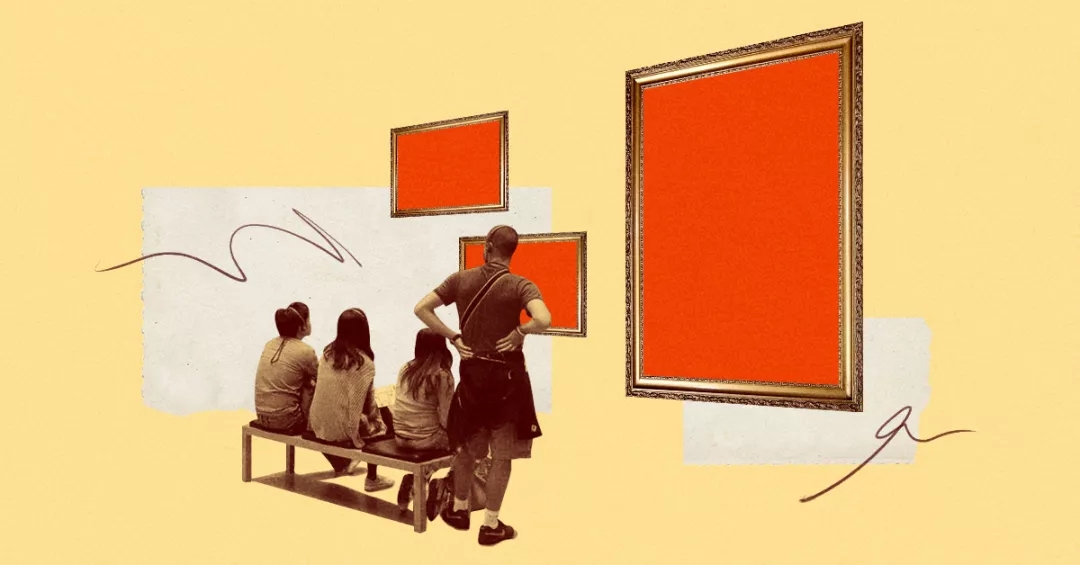
有洞察力和实践价值的
(insightful and practical)研究
这些研究的特质包括:语言简洁且令人信服、提供了出色的(深)描述、包含丰富的案例、具备重要的实践价值。这种研究大多数是质化的,往往会基于访谈、焦点小组和参与式观察,也常会结合批判视角(例如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等)来解释它收集到的实证证据。
一项研究如果想要有洞察力和实践价值,特别应该指出它的发现具有哪些实践价值、可以提升哪些特定社群的现状、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实践者更好的开展工作。它所涉及的,也一定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那些问题。

Buzzanell和Liu的论文(2005)便是一项有洞察力和实践价值的研究。他们将视角对准了女性的产假问题,并邀请了15位女性描述自己从怀孕、休产假到恢复工作的整个过程。这项研究将政策传播、女性主义等领域的知识容纳近了组织传播研究之中,为我们理解孕妇提供了重要的洞见。同时,孕妇这一群体的经历也得到了出色的描述,这当然也体现了作者强烈的道德关怀和批判性思考。

▶范文:Buzzanell, P. M., & Liu, M. (2005). Struggling with maternity leav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 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t analysis of gendered organizing.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3(1), 1–25.



 HAOAD
HAOAD